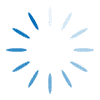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兴许早在当初你就不该留我。”抖动着的下唇似乎想要宣泄控诉,朦胧的阴影中,长而纤密的睫毛颤得那样厉害,微弓的脊背像是要被倾吐的千言万语压垮,苦涩的嘴张了又张,可最后,绫杳却只干涩地摇了摇头,垂眸间鼻音氤氲地轻笑了一声,终是塌下腰来:
“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自作聪明的跳梁小丑。”
高高扬起的脖颈线条如新,黑暗的剪影轮廓中,平日颇有锻炼的紧致的身体线条不似官家小姐过于纤细的弱柳扶风,此刻却若易折易失的纸鸢,在凌厉的大风天摇摆无依:“我现下方才明白,能与神像摆在一齐的,终归是另一座神像。”
“就像我永远不会是神荼…也不能是神荼,有些人一旦死了,就意味着她会永远而清晰地活着,不是吗?”
玄桓心下猛地再度揪痛,斑斓的情绪翻滚着令他想要狠狠呕出心中的那口污血,却终究与面上故作的平静割裂,泾渭分明。
绫杳并不识情爱,可他该懂事。
几乎要违背理智咬紧的牙关催着他的语气一下子加快,就似乎只要慢上一秒,心中始终翻腾的郁气便会激烈地破土而出,摧残他的最后一丝理智,裹挟着不顾一切也摧毁一切的感性与疯狂,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入无法挽回的深渊:“…可是人生不只有爱,杳杳,你还有你的人生,你在来到青崖镇之前所钟爱的一切…没有人会因为失去爱而活不下去——”
“可你呢玄桓…!…可你呢?!”
愤怒之下被猛然揪起的衣领几乎狼狈地要勒断他的脖颈,玄桓粗喘着气,看着那手臂上渗溢的血珠终究滚落下来,就像那滴一齐打在他脸上的热泪:“你分明是为了她而活,也为了她而死…”
“你又何曾脱离了爱而活了下去…自她死后,你不过是一副行尸走肉!”
可最先跳入这场深渊的,分明是他。
“正因为不爱,所以我永远求不得那样的公平…”
…那样为之生死的公平。
在身下之人开口之前,绫杳颊边垂着一滴欲坠不坠的泪,却恶狠狠抓着男人皱乱的衣襟迅速俯身,吻住了那张向来理智又伤人的嘴,狼藉的散乱中,两人交迭的喘息愈发浓烈,衣料摩梭的声响热烈,心与心的交迭似乎在某一瞬间达成了一致的频率,酸涩与掩不住的咸流转于笨拙触弄对方口齿的舌肉之间,齐整的银牙直至在将要窒息的那一刻猝不及防地对着玄桓狠狠咬下,抓着男人臂弯的小手几乎要将手下的那块皮肉拧至青紫——
身下之人吃疼地闷哼一声,在深深的伤口渗溢出鲜血之前,绫杳喘息着扯下胸前最后一丝遮掩的布料,慌乱般将那方桃红色的布料狠狠将其塞进了男人的口中。
她害怕被拒绝…至少,在今夜。
床不远的阴影处,摆着一方空荡荡的小柜,绫杳翻过身来赤脚走下,在再度闪起的电光雷鸣中,踏着一地碎裂的琉璃,捡起了阴影深处某个被摔裂出一方小口,却仍残留半盏酒液的小瓶,一饮而尽。
冰凉的酒液柔顺入口,灼烧的激烈却像是从喉管一路而下,直至炽热大火包裹了每一条流动的血管。
目眩之中,她垂眸看见了那个,被摔散在地的榫卯小球,还有那封在黑暗中孤零零掉落在地的,扉页半开间似乎写着她名字的绯色婚书。
…原来他早就知道。
绫杳泪眼模糊地蓦然笑了,脚底再度被割破的地方,在冰冷的地上,留下一个个不完整的、踏向床榻的血色脚印。
脖颈再度被温热的呼吸轻抚的时候,被长鞭牢牢锁着咽喉的玄桓难以抑制地轻颤了一下,垂落的长发与男人颈间的一模一样发色长丝凌乱交缠,似乎是龙凤烛影中交杯对酌的结发夫妻,玄桓却只能僵梗着脖子无力地注视着这一切,女子酒意升腾中漾开一抹虚幻空无的笑容,轻覆在身上的娇小身影轻轻揽过他的脖颈,再度垂眸用力的吻过了他的紧绷的颈侧,瀑散的青丝就这样流溢着,盖住了她耳垂下那颗一闪而过的朱砂小痣。
她的耳洞是空的。
玄桓被这同样一闪而逝的发现晃住了神思。
“玄桓…玄桓……”
她喘息着侧头吻着他的脖颈,玄桓身上独有的竹香、木香,混着后知后觉地汗意,与大漠往来的风,与茶香酒意一齐,萦绕成一股她这辈子都难以忘却的味道,喃喃的酒意打在他的身上,此刻确乎确确实实醉去的女子就这样软在他的身上,口中不断唤着他的名字,到底是青涩而单纯的未出阁的女子,玄桓心下侥幸,眼见着娇小的身影在酒意发作间眼皮打架,似乎未有下一步的动作——
然下一刻绫杳迷迷糊糊直起身来,猛然割破手腕的动作却霎那将他升腾起来侥幸摔了个粉碎。
他竟没有发觉,绫杳俯身去拾那酒瓶之时还藏了一块尖锐的琉璃碎片在手中!
伤口不算深,却满是要紧的大血管,浑身灼热的血像是在那一瞬间冷了个透,玄桓挣扎着,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垂落的手腕处的血越流越多,比他毒发时呕出的毒血更多也更鲜活地,浸透了他的整个衣襟。
最后的小裤不知在何时被扯落,远远踢到床脚,身上之人分明是笑着的,玄桓却只觉得比方才的疯狂更冷,徒留下的欲混着鼻尖新鲜的血腥气味,钳住了他瘫痪多年的腰下,青涩地磨弄几下,抬起的小腰笨拙地擦过几回,终是在天青长眸的紧缩中,反手攥着固定,朝着即便已然被这突变吓到萎靡几分都勃大到难以置信握下的欲根狠狠坐落。
“你瞧…玄桓,也有人为了你去死呢。”
霎那的猛然坐落,几乎在一瞬间将身下保存多年的处子膜撕裂,随着惯性势如破竹般狠狠顶进了甬道的最深处,绫杳疼得无法自抑地深深弓起腰来,失控地落下满脸的泪,近乎要将身下紧攥的衣袍扯烂。
似乎精神上的疼比起此刻身体的剧痛还要弱上不少,梦中几番湿润开拓都无法得入的粗大肉棒此刻却在毫无前戏之下强硬地将仅有几分潮意的穴道一举插了个透,若是此刻的光线好些,甚至可以瞧见女子双腿间的平日两指都难入的小洞此刻却被某根粗大到骇人的欲根生生撑开,穴口处虽侥幸没有撕裂,两片娇小的阴唇都似乎因着人满为患被可怜兮兮地挤出家门,被绷到已然发白的肉膜预示着此间极限,凄惨到似乎只要这根闯入穴内的巨物动上一动,就能将这不知死活的膜口生生捣烂。
“绫杳…!唔…啊…你真是…疯了!!你…真是个疯子!…”
身下之人愈发猛烈地挣扎起来,可就算被粗粝的长鞭磨破皮肤,易碎到比书生都孱弱几分的肉体却哪能挣脱这不知从何而来的上界法器,手背及脖颈之上瞬然暴怒的青筋标识这玄桓从未有过的失态,气得周身俱颤,玄桓好容易将口中的桎梏摆脱的一瞬,便是如一个当街泼妇一般,毫无形象地破口大骂。
他甚至难以去想这种从未有过的暴怒是因着对方毫无顾忌的自杀行为,还是明知两人已然未有可能,却顶着报复他的名头来毁了自己的一生——
饶使深居简出,他还是对人族道修对于破了童子功的失贞之人的残忍迫害耳闻不少。
剥皮、抽骨、剔除灵根…乃至于如同食用鱼生般地活剐……
饶使女子的贞洁从来不在罗裙之下。
他却还是曾在两人险些擦枪走火后的某个午夜梦回汗涔涔地惊醒,在他已然身重魔毒尸骨无存的时间中,天赋灵根的绫杳只是因着少了那颗代表‘心无杂念,一心求道’的朱砂痣,在无数人或惋惜、或窃喜、或不忍直视的目光下,被一凿一凿,生生钉死在兑泽山门的石壁之上,发暗的鲜血染红了一片石壁。
他舌上被咬伤的伤口很深…却不及她手腕上血肉模糊的伤口深。
不知极致地痛过多久之后,她含着泪弓起身来定定看着他,闻言却歪头笑了一下,那双混沌杏眸内却满是无所谓的漠然,用那只依旧流着血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玄桓瞬然僵着,生怕他再有的动作撕大了她的伤口。
“嘘…你好吵。”
她染血的指尖点在他的唇上:“我不会死的,玄桓…我只是在还债,还我欠你的债,我情愿他人欠我,我也不会欠他人——”
纤细的,沾满粘稠鲜血的指尖旋即抚过床栏上,被长鞭死死束缚的男人臂上一新一旧的两条疤,旧的那条是郊狼帮他们互相挡刀的那一日留下的,而新的那条,则是血月那一晚他寻她回来时留下的,偏偏的,读书写字之人的右臂最为珍贵,却都偏偏扎扎实实地砍在了右臂。
“你若觉得不够…我大可以在另一只手再划一刀,偿到你满意。”
一手可握的滑腻的乳肉似乎比梦中还要娇嫩美好,尖端像是坠着一滴红蓼,颤颤地隔着染血的衣襟紧贴在他的胸膛之上,往日总是那样娇艳的脸庞此刻却已然因着失血过多晕出透明无力的苍白,见着身上之人随着话音落下再度起身,玄桓甚至顾不得牵动那已然有些血痂的伤口,急声说了句不。
他的干涩的唇上,染着她指尖留下的血。
绫杳觑着那道血痕,垂首吻去。
极致的疼痛消去,终是缓缓适应入侵者的甬道自我保护般泌出一股又一股透明的润滑液来,却仍旧因着这般非人的尺寸好似整个人被从中撑开,生生剖裂成两半,过于可怖的硕大甚至将跨坐在上的女子清瘦而单薄小腹都顶出一道清晰的柱状轮廓,依着传统的阴阳之修的结论,女上位最是深入,饶使这般,却还未有到底,染着大量血丝粘稠清液的耻毛之上,足足仍还有四分之一的长度遗留在外。
绫杳忍着被生生剖开的不适,放任腕间的伤口流血或结痂,躬身双手紧抓着玄桓紧绷的肩头,眯眼回忆着话本中的描述,半跪着抬臀抽出些许,厮磨着再度坐落。
散乱的长发已然半干,女子此刻的额间却浸满了新出的汗。
一下一下,她尝试动作着,酒意的再度上涌似乎冲淡了身体被侵犯的不适,绫杳忍不住仰颈大口喘息着,直至在某一滴汗坠落的下一秒,黑暗中那颗覆于耳下的朱砂痣终是随着滚落的汗珠,一齐消散了个干净。
“今夜过后…绫杳还是绫杳,玄桓还是玄桓,我们从未相识。”
沾染干涸血液的小手抚上小腹,随着身下交合的律动与耳边逐渐粘稠的皮肉相触的啪啪声响闭眼感受着内里的动静,混沌中便好似腹中早已怀上了一个足月到已然会动的胎儿,女子的喘息声尾音带着几分平日难以得见的娇腻,喘息间说出的话却又那样的冷:
“若有了孩儿,我会生下来…只会告诉他,嗯…啊…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会作为你的血脉再度留下去,他会娶妻生子,孩子的孩子还会有孩子——”
“…他们…生生世世…将成为你背叛爱人的证据…”
——————
尒説+影視:p○18.red「po18red」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