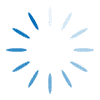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臣……是臣不好。”
是他心急了,她早就同他说过,她对他没有男女之情,是他说也许她会对自己日久生情,这一切都是他强求来的。
如今他更是不应该逼她,他应当给她些时间才对。
裴词安舍不得看见沈若怜受一点儿委屈,可一想到如今她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都是拜自己所赐,他心里就愈发愧疚。
“公主……”
小姑娘瞪着一双水蒙蒙的眼睛看他,吸了吸泛红的小鼻尖,声音带着鼻腔,“以后不准你这样逗我了。”
她没哭出来,方才见裴词安那副局促的样子,她忽然又觉得有些想笑,倒也没那么委屈了,况且,他也没做错什么。
想了想,沈若怜又补了一句,“罚你待会儿给我去泰和饭庄买个冰糖肘子。”
她的嗓音糯糯的,说话的语气也娇娇软软的,尾音带着一丝俏皮,裴词安心里一软,笑看着她:
“臣、遵旨。”
沈若怜“噗嗤”一声笑出来,故作夸张地叉着腰瞪了他一眼,嗔道:
“你怎么现在这么油嘴滑舌啦。”
小姑娘眼角还有些微微的嫣红,这一眼瞪过来,又娇又媚,裴词安掩下心底的悸动,拍了拍她的脑袋,“走吧,回去换了衣裳,给你去酒楼买冰糖肘子。”
他知道沈若怜十分看重他这个“朋友”,就跟看重白玥薇一样,也正是她把他当做朋友,才对他没有太多男女大防。
可她还不喜欢他,所以还接受不了他突然认真的亲近或深情。
裴词安看着在前面走着的沈若怜,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再不能这般莽撞和唐突了,免得再吓到她。
这般想着,不知为何,裴词安又下意识朝不远处的二楼上看了一眼,却发现那里早就没了太子的人影儿,只有檐下的羊角灯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着。
等到两人回到休息的雅间时,晏温已经带着人离开了。
沈若怜松了口气,和裴词安各自换了常服,自有招待的应侍给他们端来茶水点心。
两人边吃边等,小半个时辰后白玥薇和褚钰琛也回来了。
四人一合计,反正要去买冰糖肘子,不然就顺路去泰和饭庄将晚饭一并解决了。
-
夕阳在宽敞的朱雀大街上铺了薄薄一层碎金。
喧嚣的街市上,有些路远的小摊贩已经开始收起了摊子,准备提前赶路回家,倒是两旁的酒楼茶肆逐渐迎来送往逐渐热闹起来,再远处的人家三三两两升起了炊烟。
春日的黄昏,在橙色的天空下,有种特别的生机与活力。
一驾繁贵富丽的马车缓缓从朱雀大街的南端驶来。
晏温坐在马车里,夕阳从半开的车窗投射在他对面的小几上,给马车里也染上了一丝温情。
他慵懒地倚着引枕,微掀眼帘,索然无味地透过车窗看向外面的街景,眸子里一片寡淡,好似这繁盛热闹的市井生活,并不能引起他情绪上的半分波动。
马车转了个弯儿,夕阳投在晏温的左手上,他感觉到一丝暖意,张开手心,垂眸看了眼掌心,唇角忽然扯出一个淡漠的笑意。
二十四年皇宫生活,十六年储君之位,他深信自己早已变得冷静自持,事实上,他在政事上的确严明冷血,从未出过任何披露,他也力图去扮演好一个温润仁厚的上位者。
可他最近越发觉得从前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他开始怀念那年战场上的生杀予夺,进攻、侵略、掠夺,任何一个字眼此刻想起来,都令他热血沸腾。
马车缓缓停下,李福安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殿下,到了。”
晏温收紧掌心,声音里含着愉快地笑意,“知道了。”
李福安不知道殿下在笑什么。
他跟着晏温下了马车,一道走进街边一个写着“金玉满堂”的铺子。
还没进去,方掌柜就一脸笑意迎了出来,作势就要跪,被晏温拦住了,他只得躬身对晏温行了一礼,“殿下您怎亲自来了,快请进来上座。”
晏温虚扶了方掌柜一把,温声笑道:
“孤今日出来办事,恰好路过,便想着不麻烦方掌柜再遣人送一遭了。”
方掌柜忍不住悄悄睨了晏温一眼,见他眉眼温和,神色沉稳端方,丝毫没有他从前见的那些纨绔的架子。
方掌柜心中不由愈发敬重,忙叫伙计将东西送来,双手呈了上去,恭敬道:
“殿下您瞧,这是您上次差人送来的翡翠,小的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让他们打了这一副耳坠和发簪,你看看可能入得了您的眼。”
恰在此时,小二捧了茶过来,因为太过紧张,给晏温倒茶时险些洒在了外面,晏温笑着虚扶了一下,对那小二十分温和地道了声,“有劳了。”
那小二一怔,面上竟生出了一抹红晕,一叠声地说着“多谢殿下。”
小二倒了茶退下后,晏温拿过托盘里的那支玉簪揣摩了半晌,放回去,笑道:
“甚合孤的心意,李福安,赏。”
方掌柜闻言一颗提在喉咙眼的心瞬间落回了肚子里,急忙跪下谢了恩,接过赏赐,亲自去将那副耳坠和发簪打包。
临走前还热情地让晏温先喝茶,说这茶是他岭南老家亲戚托人送来的,虽然卖相差些,却口感回甘,十分好喝。
见晏温笑着应了,方掌柜喜滋滋便去了后面包东西。
待到方掌柜走了,李福安觑了眼晏温,犹豫道:
“殿下,这茶——”
太子在某些方面十分讲究,比如这茶是断断入不了他的眼的,更何况这茶具也不是他常用的。
晏温笑看着李福安,神情愉悦,“方掌柜既说是岭南来的好茶,福安还不赶快尝尝。”
李福安:……
他就知道,这种事哪次少得了他的。
方掌柜包完东西回来,见桌上的茶果然被喝个干净,心里又感动又激动,急忙就要让小二将后院房里放的那一包茶叶都拿来,要敬献给太子。
李福安眼角抽了抽,没等晏温说话,自己先开了口,“方掌柜不必客气,您这茶自己留着喝就行,太子殿下他——近日胃寒,宫里给开了养胃的药,这绿茶实不宜多喝。”
他对方掌柜说着话,极力忽视太子对他微微挑眉十分好整以暇的样子。
方掌柜听完,哀叹一声,说都怪自己不知道,还让殿下喝了这茶。
晏温淡淡一笑,“无妨,你也是一片好心。”
说着,他视线一转,指了指一旁柜台,“这镯子看着十分别致,孤能否看一看?”
李福安和方掌柜不约而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见那柜台上放着一个红木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只鎏金镂空手镯。
那手镯上的纹样是两枝缠绕的藤蔓,而在手镯最下方,还坠着一朵并蒂莲,并蒂莲的莲心分别点了一颗红宝石和一颗蓝宝石,小小的,却十分精致。
看那手镯的尺寸,就是专给小姑娘带的。
方掌柜“哎呦”一声,走过去连同那红木盒子一块儿拿了过来,笑得谄媚,对晏温道:
“这不是巧了。”
“巧了?”
晏温拿出当中的镯子,这才发现这镂空的镯子里面还嵌了几颗小小的铃铛,他忽然就想象出沈若怜带上这个镯子的样子。
李福安问方掌柜,“这镯子怎么卖的?”
方掌柜一拍大腿,有些痛心疾首地模样,“哎哟,小的刚才说巧了,说的就是这个。”
“这镯子,是裴尚书家的裴二公子亲自设计了图样,拿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帮着打的。这——”
方掌柜偷偷看了一眼晏温的表情,声音越发低了下去,“这镯子本店没有售卖的权利。”
李福安觉得自己头皮都麻了,裴词安亲自设计的镯子,还能送给谁,怎就好死不死地被殿下看到了。
他根本不敢看太子一眼,余光瞥见他将那镯子放了回去,温润的声音里带着宽厚笑意:
“无妨,孤也就是觉得好看,欣赏一下而已,裴公子果然眼光不错。”
“诶诶。”
方掌柜将镯子收起来,交给小二放了回去。
晏温将手串抹下来,拿在手里捻了捻,慢条斯理地起身朝外走去,李福安和掌柜的一左一右跟着他。
及至走到门边的时候,晏温忽然又停了下来,顿了顿,他回头看向方掌柜,“倘若孤想打一条脚链呢?”
他停了一下,“就比如和那镯子一样的,空心的,带铃铛的。”
方掌柜认真想了想,一脸正色道: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殿下若是给脚链上嵌了铃铛,那么稍微一走路或者晃动就会发出声响,是否会有些——”
“无妨。”
方掌柜“吵”字没说完,晏温打断他的话,笑得意味深长,“就让它响。”
直到太子走出去好久,方掌柜还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脚链上加那么多铃铛。
他挠了挠头,招呼小二过来收拾东西。
晏温回到东宫未出片刻,户部的张侍郎在外求见,晏温净了手,坐到桌前,让李福安将人带进来。
户部张侍郎名唤张武,他今日本来在家待得好好的,突然被东宫的人唤进宫,说是殿下召见,一路上来的时候心中十分忐忑,也不知太子殿下亲自召见,是好事还是坏事。
虽然太子仁厚,但那威仪也不由让他心生敬畏,此刻听闻李福安让他进去,张武深吸一口气,这才轻手轻脚推门走了进去。
他跪下前抬头匆匆扫过晏温,见他正拿着一方白色的帕子擦手,面上并无不善,心下松了些,“殿下。”
“嗯。”
晏温放下帕子,让他平身,手指搭在书桌边缘点了点,才道:
“听闻京郊的丹良马场是你弟弟包下的?”
张武一愣,不知殿下为何突然问这个,如实应道:“是舍弟所承包,敢问殿下,可是这马场出了何事?”
晏温笑道:
“倒也没什么事,只是孤今日去瞧了,那马场建在云山下,如今恰逢春季多雨,那云山极易有泥石流,若是哪日伤了人便不好了。”
张武的弟弟张文去岁来找他商议承包马场之事时,两人只觉得这马场离京郊远私密性好,场子又大,十分适合做达官贵人的生意,当时两人确实没想过这一茬。
如今太子既能说了,那定是存在着大隐患的。
他一时有些后怕,不由问道:“那依着殿下的意思,这可如何是好?”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