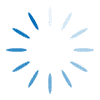太子用几乎被喉咙碾碎的声音,一字一顿道:
“孤倒要看看,她能逃到哪儿去。”
他的嗓音沙哑而冰冷。
贾柯忍不住想起自己冬日早晨天还未亮,独自一人走在空荡的街道上去上朝时,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厚厚的雪地上发出的那种声音。
他没敢再说话,低着头等了会儿,跟在太子身后出了门。
清剿逆党并未遇到阻碍,这是一群不成器的逆党,晏温早就知道这只是他皇帝老子为了支开他设的局。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他垂眸冷睨了眼下面为胜利欢呼的众人,意兴阑珊地撇开眼走下台阶。
未出片刻,一阵马蹄声响起,薛念牵着一匹黑色的汗血马到他面前,“殿下,您要的马。”
“唔。”
晏温神色有些寡淡,他淡淡的应了一声,作势就要翻身上马。
“殿下!”
晏温骑在马背上,压下眼帘看他,淡道:“如何?”
薛念犹豫了一下,“您……您手臂上的伤口还是包扎一下吧。”
晏温扫了眼伤口,冷嗤一声,淡淡撂下一句“死不了”,缠紧缰绳便策马飞奔了出去。
本应快马加鞭一天的路程,晏温用了大半天便到了。
李福安早就得了消息在宫门口候着。
他看了眼殿下胳膊上还在渗血的伤口,没敢出声,一面跟在晏温后面,一面将自己昨日如何发现嘉宁公主不见了这件事,同他详细说了一遍。
晏温没出声,就面无表情地听着,脚底下步子走得飞快。
及至到了东宫和后宫分岔路口的时候,他脚步顿了一下,而后毫不犹豫地朝凤栖宫的方向走去。
晏温没让人通禀。
皇后听说晏温来的时候,他人已经到了大殿门口,皇后再让陈莺去藏起来已是来不及。
“不必藏了。”
晏温沉冷的声音从大殿门口传来,“孤有话要问她。”
陈莺脚步一僵,面色煞白,求助一般看向皇后。
皇后面色也十分难看,她将陈莺拉到身后,安抚般拍了拍她的手,僵着嗓音问晏温,“太子如今是愈发不懂规矩了,到这凤栖殿来,也不让人通禀。”
晏温打从被封为储君后,便自来克制守礼,温润恭谦,每每来凤栖殿时也常挂着一副温和的笑容。
然而此刻的他周身散发着沉冷的森寒气息,眼神凌厉而阴桀,仿佛时刻在提醒众人他是执掌生杀大权的上位者。
凤栖殿的宫人早被骇得不由全都跪了下去。
太子冷扫了她们一眼,不回皇后的话,却是越过她,直接对她的宫人命令道:
“尔等全都下去吧,孤有话同母后说。”
皇后见他如此,面色更加难堪,握住陈莺的手不由一紧,而陈莺早就吓傻在原地,面白如纸。
待到众人都哆哆嗦嗦下去,李福安将宫门关上,偌大的宫殿里便只有太子和皇后三人。
他冷睨了她们一眼,自顾走到一旁,慢条斯理地倒了杯茶。
晶亮的茶水潺潺流入杯中,晏温忽然勾唇笑了,“陈莺,你还记得孤曾经跟你说过的话么?”
陈莺身子一抖,“噗通”跪了下去,“民女、民女……”
“太子。”
皇后将陈莺拉起来,让她坐在自己身旁,语重心长地对晏温道:
“东宫的一切,是母后逼陈莺说的,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嘉宁是你——”
皇后顿了顿,“你从小视她做亲妹妹,怎能同她……况且母后自来觉得你和善知礼,怎就竟能做出、做出那等事来!”
“妹妹又如何?!”
晏温猛地砸了茶杯,身子前倾,语气暴戾,“孤从小看着她长大,她不跟孤跟谁?!”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晏温又重新坐了回去。
好似方才那瞬间的发泄,让他一直强撑的情绪再也支撑不住了一般,他懒懒向后靠在椅背上,阖上眼眸,手背搭在眼睛上,疲累不堪。
过了好半晌,他轮廓锋利的喉结微滚,舌头顶了顶齿尖,重新睁眼看向皇后时,眼神不复方才那么犀利,哑声道:
“她都同孤有了肌肤之亲,儿臣不该将她留住么?”
“那你也不该绑着她!你这么做同那三教九流的混蛋有什么区别!”
皇后有些气怒,第一次骂了脏字,陈莺急忙扶住她替她捋了捋前胸。
晏温眼神闪烁了一下,没说话。
过了会儿,待皇后平息了,晏温对陈莺道:
“孤不动手打女人,但你是放走嘉宁的罪魁祸首,孤——”
“太子!”
皇后气急了,一拍桌子,手指颤抖着指着他:
“为着个嘉宁!你当真是疯魔了!你还记不记得陈莺的哥哥是怎么死的了?!他为了你,为了大燕的百姓而牺牲在你的箭矢之下!如今你还要对付他唯一的妹妹么?!”
晏温猛地叩紧扶手,手背上青筋虬结,眼里闪过痛苦的神色。
他不会忘记自己十五岁那年射出的那一箭,他亲手将被敌军俘虏,以此来威胁大燕士兵的陈崔射杀。
当时陈崔双目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大喊着让他快些动手。
他握箭的手颤抖不止,射出的箭却稳稳正中他眉心,从那之后,他便再也拉不开弓了。
晏温深吸一口气,沉沉看了陈莺许久,神情克制。
末了,他默不作声撑着自己起身,脚步低锵地朝殿外走去。
“殿下!”
陈莺见他要走,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忽然唤住他。
她捏了捏拳头,紧张到声音都在发颤,却还是说,“我知道殿下那日叫我去东宫是为了刺激嘉宁公主,我也能感觉到您心中是有她的。”
晏温的背影动了动,却未回头。
陈莺接着道:“您是天之骄子,一生顺遂,自来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但您可能不知,这世间唯有感情一事是强求不来的。”
“您若当真爱她,就不应当囚禁她,她不是您的所有物,更不是您的附属品,您若是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又如何想要她平等的来爱您?”
晏温猛地回头看向她,陈莺缩了缩脖子,还是说:
“您从不知道何为爱,从不知道如何才是爱,您的那些门锁、脚链,以为能将她拴在身旁,实际不过是将她推得更远。到了如此地步,您与她破镜再难重圆,不若就放她自由,相忘于江湖。”
陈莺越说声音越清亮,越说脊背挺得越直,直到她说完,大殿久久回响着她最后一句话。
晏温也久久地看向她,眸中神色模辩。
过了许久,他将腕上的佛珠摘下,拿在手中一颗颗捻过,一言不发地转身继续朝外走去。
胳膊上被血泅湿的衣裳已然干涸,隐隐散发着血腥气,他的步伐有些空洞而虚浮,身影透着莫名的疲惫。
凤栖殿的大门打开,炽烈的阳光一瞬间照进来,大殿里一片明亮,可那阳光却仿若独独绕开了他一般,在他的身上仍是只有沉冷和落寞。
晏温并未处置李福安,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他回了东宫,一句话不说,径直去了主殿。
主殿的内室,被子还是沈若怜走时铺开的佯装成睡着的样子,晏温看到床褥,眼睫轻颤,眼眶忽然有些微微发红。
他在门边站了许久,才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走过去,缓缓坐在了床边,看了那被拢成人型的被子。
过了许久,他轻轻抬手,缓而轻地抚摸上那床被子,低低呢喃。
“娇娇,孤回来了。”
晏温从回来的午后进了主殿便再也没出来,一直到天彻底黑了,李福安也不见房中点灯,犹豫了好几次,他最终还是大着胆子推门进去了。
月辉如水,落在殿中,透过一片朦胧的黑暗,李福安看到晏温竟就抱着那人型的被子合衣睡着了,似乎还怕怀中抱的“人”冷,殿下伸手拍了拍那“人”,将“人”搂得更紧了。
李福安心里酸涩不已,殿下那天夜里连夜去了耀城,第二日又忙于清剿逆党,第三日又快马加鞭赶回来,满打满算竟是三日未合眼。
他轻手轻脚走过去,小心翼翼将一床被子盖在太子身上,无声退了出去。
第二日天还未亮,晏温就从房间里出来。
他的面上看不出一丝憔悴,神色如常地去上朝,回来后吩咐暗卫所有人,除了执行任务的,其余人全去找嘉宁公主。
李福安不敢多说,只是一边跟着他往宫外走一边不住在心里叹息。
及至从东宫绕到乾坤殿的路上,皇帝跟前的张公公双手拢在身前,站得端端正正地在等着他。
晏温看他一眼,“你不必替父皇劝孤,孤无论如何也要将嘉宁找回来。”
张公公弯腰对他笑道,“老奴不是来劝殿下的,老奴是奉旨来问殿下替陛下要一句话的。”
晏温冷睨他一眼,没说话,等他的下文。
那张公公笑道:“陛下说,殿下若是此次出宫去找沈姑娘,那这太子之位便要让贤,陛下让老奴问殿下,您如何选。”
“那就让。”
晏温闻言没有一丝迟疑,冷笑,“孤还当是什么事。”
言罢,他又朝着乾坤宫的方向看了一眼,毫不犹豫地转身继续朝宫外去了。
-
八月底的江南仍然有些暑热,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整个空气都湿哒哒的,潮闷地令人有些窒息。
不过沈若怜却十分喜欢这样的天气,她生在西北的小山村,后来又在皇宫长大,总觉得这江南的烟雨朦胧充满了水墨画的典雅,十分有意境。
每每下雨的时候,淮安本地人便都蜗居在家中不出来,整个湖边就她和秋容两人。
她最喜欢的便是温一壶江南春,摆一把摇椅在湖边的亭子里看下雨,盖上薄毯,然后摇着摇着便能睡上一下午。
江南春是江南特有的果酒,味道清甜,却几乎不会醉人,连她这种不喝酒的人都可以喝上一壶。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