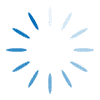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喂,说起来原来永朝明惠皇帝也是昏庸无能,诛杀无数忠臣,你好歹是将门之后,又与他有杀父之仇,为何不反?”顾寒江回去不但要经过安静的主帐,还有大堆大堆的军报等着处理,他索性离那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
“我与将军貌似,不相熟吧?”杜矜刚要起身熄两盏白烛,被按在板凳上。
顾寒江铁了心要在他这边混时间,搬了凳子坐到他身边去,“多聊聊不就熟了?那些旧相识的熟人只会给我添堵,不见也罢。”
他说这话时,脑海里只有那个放着登基大典不去,跑来边境小城“参加”婚礼的某人。
杜矜没料到这人脸皮这般厚,捱不过他,垂睑叹气,“这事哪是说得那么容易。”
这点上他就自认比不上裴慕辞。
他的命本就是清妩好不容易保下来的,他不想杀害她的家人,不想让她在看他的时候,眼中只剩下仇恨。
可即使他没有做这些,他现在还是一无所有。
“那什么事容易?”顾寒江不知道这医师是本性如此,还是这么多年被磨灭了硬气,“你就说裴元皙吧,那些年过着狗都不如的日子,还忍辱负重地在牢里蓄积力量。”
“当然这里面我出了不少力,谁让是他把我救出去的呢?”顾寒江摇头晃脑的自得一番,继续说道:“后来祁域潜伏进上京,元皙赶去汴京布防的时候差点死路上,幸好永朝皇帝微服出访,把他买下来送进公主府里当面首,虽然说出去不好听,但好歹活下来了。”
杜矜注意到他提到明惠帝的语气,好像并没有多大起伏,就像并没有接触过这人一样。
“那你们当初为何在城墙下逼死皇帝?”反正明惠帝都已经投城,又是个内虚中空的废帝,应该威胁不到他们的大计,裴慕辞看在清妩的面子上,也不该对皇帝那般决绝才是啊。
顾寒江听到此话也愣住了,仿佛听到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
“谁逼他去死了?”
杜矜刚想接着问,顾寒江突然被什么动静激怒了,拍案而起,走了几步挑开帘子,怒火中烧:“吵吵嚷嚷的作甚!都没有军规军纪的?看来是操练得不够到位!我叫人再带队去山上拉练几圈?”
他又在外面刚散训的那群人里面听到了不爱听的字眼,什么主公,什么美人。
对对对!主公正搂着美人安歇呢!
劳心劳力的都是他!还得不到一句夸!
顾寒江回来坐下,每一步都像是要把泥石子路给踏碎了,气急之下脑袋里什么都没剩下,转头问杜矜,“你刚刚说什么了?”
——
丑时。
主帐的烛灯还剩了几盏,昏暗的像是丛林中密密麻麻的小飞虫罩在头顶上。
裴慕辞骤然睁开眼,摸到身边的被褥冰冷一片。
他连外袍都来不及披上,快速起身塞好鞋袜,拿起披风匆匆扬在身后,出帐去找人。
清妩正和下训的将士们围坐在一起聊天,徐莺陪在一旁。
凌晨的凉风总比白天的穿透力更强,估计着还有两个女孩子坐在那,有士兵搬来些枯木,打算生个火堆。
坐在清妩旁边的男孩年纪很小,侧颊有些雀斑,拿着一布袋的干粮往火里倒。
围坐的士兵俯身,把滚落出来的红薯土豆往回捡。
“军中的厨房我们进不去,姑娘将就下。”他们并不晓得清妩是什么身份,只知道主公这趟便是专门来渠州接她的,再加上徐莺又是州牧夫人,两个人都怠慢不得。
清妩不在意的笑笑,清冷的眉眼展开,双颊被火堆映的红扑扑的。
挨近的几个士兵眼睛都看直了,在官阶较大的那人示意下,赶紧收回视线。
清妩拿了跟小棍棍,百无聊赖的戳着火堆,趁机套话:“你知道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那个医师在哪嘛?”
她也觉得脑海里有关于徐莺的片段,可就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
“公子吩咐过,姑娘只能呆在主帐附近,其余地方还是不要去了。”徐莺勾起标准化的笑容,直接了当的拒绝她。
清妩担心杜矜因她受苦,但是又打听不到他在哪。
火堆忽然炸出一片飞屑,她被吓了一跳,心神不宁的盯着前方,焦躁感被无数微小的声音不断放大,她忽然开口问道:“有酒吗?”
众人一听她能喝酒,皆是起哄,徐莺无奈之下起身去寻。
毕竟裴慕辞只吩咐了不许公主离主帐太远,并没有限制她其余的事。
徐莺还在赤玉阁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有关于容昭公主的传闻,上次公子带人去的时候,她也不敢多看,如今近距离接触了,才发觉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她回来的时候,也不知是哪个士兵把珍藏许久的好酒拿出来,清妩已经喝上了,双颊边像是铺上了一层水胭脂。
军里的酒令没有文人雅士那么多的花样,输的人也不多喝,就在圈子里随便选一个人比武。
到头来喝的最多的竟是一心就想把自己灌醉,一醉解千愁的清妩。
年纪小的那个士兵蛮力大,和年长几岁的比摔跤也一点不落下风。
输的人不服气,又要比剑术。
他们都是军营里长大的莽撞汉子,热了之后都撸起袖子,后来摔跤的时候衣服沾上灰,干脆脱了上衣光着膀子,露出古铜色的皮肤。
不得不说,长期操练的人,身上的肌肉线条都会格外明显,看起来手感就很好。
清妩坐在角落里,双眸中带着一层水汽,眼神飘离,酒意正浓。
也不知是酒精作祟,还是面前的选择太多,她竟看不清具体的样子,只盯着眼前一片的白花花。
比完一场后,她用戳火堆的棍棍,去指点普通士兵的动作,惹来一群人崇拜的呼声。
受教的士兵纷纷上前来给她敬酒,捧着她亲自做个示范。
清妩在杜矜的管束下许久没沾酒,如今不过喝了几杯头便有些沉了。
只是那些招式早就刻在骨子里,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完整的做出来。
“姑娘还会醉拳?”士兵跟在她身后比划。
“什么醉拳,就是喝多了!”徐莺上去扶住清妩,稍微走开几步,与这群赤.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拉开距离,“别让她喝了,待会主子问你们罪。”
话音未落,就看见裴慕辞朝这里走过来。
他寻着光亮,从暗影里踱步而出,神色阴郁的能滴出水。
平日里没怎么见过他的士兵都怕得很,情不自禁的往后退了一小步。
裴慕辞却没在意他们,只向她招手,“过来。”
清妩站在远处,手里还捏着那根棍子,眼眸惺忪的望着他。
醉酒之后,她瞳孔里倒有了几分原来看他的感觉。
裴慕辞见她不动,只好走过去牵她。
清妩晃了两下,站都站不稳了,无奈之下抓住裴慕辞递过来的手,紧紧交握,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嗯?”她眼睛里亮晶晶的,一脸娇憨。
所有人都没警醒留意的时候,她二指快速捏住裴慕辞的下巴,让他与自己对视。
她脸上微带着酒晕,哼笑两声:“这个小郎君好看,比刚刚那些都好看!”
裴慕辞眉心都没动一下,当着众人的面给她披上披风,系好领口的带子。
他身量高出清妩不少,披风的后摆就曳在地上。
“好松。”她不满地踢踢拖尾,又要去扯刚拴好的系带。
裴慕辞稍微调整了两下松紧,打横将她抱起,柔软的脸颊贴在他心口,单薄的衣料透来独属于她的温度。
“刚刚喝酒的,都去领二十军杖。”
士兵们快速穿好上衣,眼巴巴地望着那个军衔最高的人。
“主公...那个、我们都没喝酒呀,我们就是拿茶水陪姑娘喝。”
那人一句话一顿,徐莺看不下去,帮忙解释了两句,“主子,是姑娘心情不好要酒喝,也怪我没有看好,让她喝了这么多,公子正在气头上,要罚就罚我——”
她的“吧”字还没出来,就被一声娇喝打断。
清妩从裴慕辞怀里抬起头,咋咋呼呼的叫徐莺的名字。
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动作,把她看着。
众目睽睽之下,清妩攥着裴慕辞的衣领,像是根本看不清一样,手指随意点了几个还来不及套衣服的士兵。
“莺娘!这几个郎君不错,你得给我留着!”
徐莺抿起嘴不敢说话,也不敢去看裴慕辞发青的脸色。
——
裴慕辞想着现在与南朝隔河对峙,前线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到底也没有罚这些人,甚至还允许他们继续呆在那,把剩余的烤物吃完。
他抱着人主帐方向走,途中埋头啄了一下她的嘴角。
只有一股浓烈的酒香。
想必方才也是没吃什么东西,光喝酒去了!
裴慕辞怕她等会会饿,将她抱到小厨房里坐着,走到烧壶边给她熬醒酒汤。
过几日有场决一胜负的大战,将士们都说想吃一次汤圆,所以厨房里的厨子将没用完的糯米粉和馅料剩在备料台上,等着明日好随时取用。
裴慕辞亲自洗手弄了几个,盖上锅盖。
清妩乖乖坐在灶台前烧火的小凳上,脸颊泛着红霞,黑瀑的长发散在肩后,两眼迷离,含着几分慵懒的娇艳姿态,似醉非醉的打量着他。
真好看。
无论是方才给她系披风,还是当下做的这些面点活,他神情都从容不迫,好似什么都难不倒他一样。
许是她的目光太过明显,裴慕辞俯下身,用薄唇印上她的。
清妩躲闪了一下,面带疑惑地抬头,见到是他之后,闭上了眼。
裴慕辞像是受到了鼓励,直接抬起她的后颈,将两人的距离扯近。
略带寒意的舌尖卷住她,药香与酒香在窄小的空间中交渡,舌尖徐徐探出,安抚了她急促的呼吸声。
舌尖蹭过上颚,无法抑制的痒意窜向脊柱,宛若瞬间跌进海里。
她不断向幽深的海底沉去,而他紧密相随。
清妩喘不过气,只能依赖于他渡来的新鲜空气,慢慢开始主动在他口里掠夺。
竟像是在向他索取。
“殿下,叫叫我吧。”无人可见的厨房角落,裴慕辞的神色和语气,都带着无比期盼的怜求。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