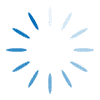写在前面:
从2009年开始到2011年出本,又到了现在的2022年,时间过得好快。
在几番思索后,我决定全文公开在网路上,谢谢当年支持我的朋友们,也谢谢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朋友,我很珍惜当年的盗墓圈,甚至有很多当时认识的人,现在还是我重要的朋友。
这几年我试图在原创的领域找到一条路,现在还在摸索。目前的根据地在这里:
http://vomisa72.blog138.fc2.com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
2022/3/12
61.
当解连环完全被沙土掩埋后,三叔站起身,默默凝视了那隆起的土堆好一阵子。
「吴邪。」
我连忙上前。
「解连环他……不是这样的人。」三叔沉默了一下:「我不希望你对他的记忆……」
三叔突兀的停顿。
「你还记得李沉舟吗,吴邪?」
有些迟疑,我没有立刻搭话。解连环和李沉舟,不是同一个人吗?
三叔轻描淡写:「记得李沉舟,忘了解连环吧。」
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记得李沉舟,忘了解连环。
但这会是解连环要的吗?解连环和李沉舟,这两个身份真的可以这样一刀分开吗?我们真的能知道另一个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吗?还是我们都只是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其实我们对于彼此一无所知?
记得李沉舟,忘了解连环。不论认同与否,这句话在我心里不断回盪。
闷油瓶开始带领我们离开瓜子山尸洞。然而,出去的过程却远比我们想像中困难。解连环设置的炸弹,虽然没有直接对我们造成伤害,却摧毁了瓜子山尸洞的主要骨干,将尸洞轰得倾颓破败。不是这边的墓穴塌了一半,堵去出路,就是那边出口的机关毁坏,完全卡死打不开。闷油瓶带着我们在墓穴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却不断碰壁。
徒劳无功地试了不知道多久,闷油瓶停下脚步,让我跟三叔席地而坐,休息片刻。三叔没有质问闷油瓶接下来该怎么办,或是我们该往哪里走。他只是静静坐着,一言不发。我想三叔他累了。闷油瓶看起来状况很不妙。而我,除去伤处的痛楚之外,身体也不大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症状我不确定,但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感觉头重脚轻,偶而还会眼前发黑。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闷油瓶和三叔各有心事在烦恼着,我不应该增加他们的负担。
事后我被三叔狠狠教训了一遍,说有异状当然要直接讲啊,憋着病又不会自己好。
但那是事后。当下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坐着,希望休息一阵子之后症状自然会过去。然而,我却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很冷,我觉得很冷。我必须要全力克制自己,才能避免上下排的牙齿咯咯打颤。
当闷油瓶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时,我挣扎着站起身,好奇怪,闷油瓶的身影在晃,怎么在晃……?
「吴邪!」
我隐约记得有人扶住了我,大声地喊叫,但是我却无法理解对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只觉得很冷,非常冷,我用双臂紧紧环绕自己,但是还是好冷,太冷了,怎么会这么冷?我听到身边有快速交谈的声音,几个字眼传入我的耳中:发烧。继续前进。休息。吴邪。我不认为这些字眼连贯起来包含了任何的意义。
三叔在叫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叫我呢?我想睡一下。好冷。
我背他。有人这么说道。
这个声音好熟悉,好像闷油瓶的声音……好像的确是闷油瓶的声音。我好像记得有什么事情很重要,跟闷油瓶有关……有人抓住我的手,让我靠在什么东西的上面。我头痛,而且头晕……三叔!
我猛然睁开眼睛,用力反握那握着我的手,三叔的脸在我面前出现。
「不要杀他!三叔,不要杀他!」
三叔被我吓了一跳,瞪大眼睛看着我。
「不要杀他!三叔!他不可能……不可能害死爷爷!」
「大姪子……」
「不要杀他!答应我你不会杀他!」
「……我不会杀他,吴邪。」
「那不是他的错。」
「我知道。」
「那不是他的错。」眼皮很沉重,我闭上眼睛,却执拗地重复道:「不是他的错……」
那不是他的错,是父亲的错。不对,不是父亲的错。是别人。谁呢?父亲有一隻黑猫。不对,也不是牠的错,牠很多年前就死了。小狗圆舞曲,不对,我们家只有猫。
我头痛。到底是谁一直晃?不要再走了。我头好痛。
我的意识变得非常模糊,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回到了吴家本家,在长长的回廊里走动,回廊比我印象中的还要长,永无止尽。基于某种不可解的原因,我停下脚步,悄悄地推开厚重的木门。
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床上,捲曲的黑色长发像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觉得她看起来很美。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却毫无光彩,一隻手不自然的垂在地上,指尖轻触地面。
她看起来苍白又纤细,有一种透明的优雅,像盛开的白色铃兰,她的头微微倾斜,予人一种不协调,却梦幻的美感。
然后,毫无预警的,从她的双眼,艳红的鲜血泉涌而出,滑过脸庞。我吓了一大跳,倒吸一口气,退了好几步,想尖叫,却只发出嘶声。
她死了。她已经死了。
然后我撞到了某个人,瑟缩一下,我却不敢回头。我知道,我身后的是谁,那芒刺在背的穿透性视线,是他,是他,果然是他。我一直都知道,是他,害死了我的母亲,他的妻子。
我突然感觉有人用湿布正在擦我的嘴唇,怎么会有人用湿布碰我呢?迷迷糊糊的,我睁开双眼。刚才那是梦吗?我做了梦?那个女人……还有……还有什么呢?
「吴邪,你醒了?」闷油瓶的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奇怪,我不是在吴家本家吗?
「大姪子?」三叔的脸也出现在视线里了,真是奇怪,我还在做梦吗?
我舔了舔乾裂的嘴巴,闷油瓶连忙再用水沾湿我的嘴唇:「吴邪?你听得见吗?」
「……是他……是他。」凝视着闷油瓶,我喃喃重复。
闷油瓶皱起眉头,一隻手伸过来,摸在我的额头上。他的手很凉。
我的视线转向三叔,喉咙感到一阵烧灼:「我一直都知道是他……」
三叔一脸茫然的看着我,混杂了担忧和恐惧。他转而望向闷油瓶,两人交换了一个忧心的眼神。
「Will all great Neptune’s ocean wash this blood clean……No. Never.」我模糊不清地说着。
眼皮沉重,我很快的再度闭起双眼,我想再见见她,就算一眼也好。我对她印象是如此模糊。
「……他说什么?」隐约间,我好像听到三叔这么轻声询问。
「《马克白》。吴邪很喜欢莎士比亚吗?」闷油瓶小声反问。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有点生气,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怎么都没仔细听呢?是他,是他做的,罪无可赦。他是……是谁呢?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做了什么呢?我好疲倦,虽然生气,但是我好累,我……
我回到了胖葵在海边的坟地,我沿着墓碑一块一块的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样都找不到胖葵的墓。天很黑,海面疯狂的捲起大浪,风像受伤的野兽一般惨叫哀嚎着。
有人在身后追我,我发疯似的奔跑着,但是怎么样都跑不快。我越是拚命,跑得越缓慢。
「你为什么不死呢?你这该死的!」我听见解连环的声音在我背后怒吼如雷,是解连环在追我。
一道闪电像是三叉戟般劈开天际。
「……对不起、对不起……对、对不起……」我呻吟着,挣扎着。
我怎么都找不到胖葵的墓,胖葵的墓不见了!在哪里呢?在哪里?为什么找不到?
「你以为你会被原谅吗?你不会被原谅的!」解连环的声音如隆隆雷声贯耳。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你去死吧……不,你知道什么吗?我希望你别死,我希望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一辈子愧疚,一辈子挣扎,吴邪!我祝你长命百岁!」
解连环歇斯底里的笑声逼得我几乎发狂。找不到,找不到,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找不到?
「不、不要……我……」我哀求着,颤抖着。
我受不了了,我逃不过了,我……
「吴邪,吴邪。」
有人摇着我,我的头剧烈的疼痛了起来。
「吴邪?」
我挣扎着,像溺水的泳者,拚命想浮出水面。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睁开眼睛,光线好亮,我看不清楚。我的头好痛,喉咙像有把火在熊熊燃烧。
冰凉的手掌又再度触碰我的前额。我不安地扭动着,神经质的重复:「……找不到,我怎么样都找不到,找不到……」
「那是梦,吴邪。一场梦。」闷油瓶轻声说道。
「我觉得她恨我。她跟他一样恨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没有人恨你,吴邪。那是一场恶梦,没事的。」
「他们恨我,喔,天啊,他们恨我……」
「没事,没事了。」
「我不恨他们,我甚至……我甚至很喜欢他们,但是他们恨我,你懂吗,他们恨我!」
有一双宽阔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我感觉到那双手上传来的温度与力道,以及粗糙的硬茧。基于某种不可解的原因,我放松了许多,好像我不再是一个人,好像有人能理解我的恐惧和痛苦。
我觉得安心了下来,朦朦胧胧的又睡着了。
我的头、手、脚都很沉,我一点也不想移动他们。我想躺着,一直躺着,不要动。
但是我突然觉得有人在凝视我,那种凝视彷彿穿透一切,令人不舒服。于是我勉强抬起头,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盯着我。
彷彿注意到我的视线,那人飞快的背过身去,迅速离去。
我瞪大了眼,不敢相信。那个身高、那个衣服、那个背影。天!那是解子扬!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而且这些年来,他都没有老,还是我记忆的那个样子!
我想叫唤他,但是喉咙却哽住了,发不出声音。解子扬背着我,越离越远。
「不……不……」
我扯开喉咙,嘶声喊道。但是解子扬越走越快,眼看他小小的身影就要消失了,我拚命的想爬起身,去追他,留住他。
「别……不要……」
解子扬走得更快了,完全无视我的哭喊,马上就要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回……回来……」
为什么不理我呢?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没有,回头,看一眼我?
然后我想起解连环的话。他说,你以为你会被原谅吗?
我感觉眼泪从我的脸颊滑落,我不希望被原谅,但是,但是……
「不要走!」
我听见我自己尖叫着,尖叫声回盪在墓穴里。我哭着醒来,崩溃地喊叫着。又是另一场梦,然而即便是在梦里,我依旧无路可逃。
我突然被拥进一个温暖的怀抱,对方紧紧的抱着我,一言不发。我花了一阵子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梦,而抱着我的人是闷油瓶。
「他走了……走了……我求他……他还是走了……」我哽噎着:「他连回头也不愿意……」
闷油瓶没有说话,只是将我抱紧。
「他连一眼都不看我……」
环绕着我的双臂圈的更紧。
「他恨我……他是不是也很恨我……」
没有回答,闷油瓶只是紧紧的拥抱我,彷彿这样就可以分享我的哀伤,带走我的痛苦。
「对不起……对不起……」
闷油瓶放任我在他怀里,半是梦囈,半是无理取闹的发赖。直到我累了,安静下来,缓缓滑入梦乡之际,他突然发了话。低沉温柔的嗓音,用法文唸起了什么,像是摇篮曲一般,哄我入睡。
──Quand tu regarderas le ciel, la nuit…
(夜晚,每当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闷油瓶轻声的说道,他的法文稍稍带了点腔,但是很好听。
──puisque j'habiterai dans l'une d'elles, puisque je rirai dans l'une d'elles, alors ce sera pour toi comme si riaient toutes les étoiles. Tu auras, toi, des étoiles qui savent rire!
(因为我会住在其中一颗星球上,而我会在那一颗星球上开心地笑着。对你而言,就会像是星星在天空上微笑一样,你拥有整片对你开怀大笑的星空。)
那是《Le Petit Prince》。那是小王子离开前,对飞行员说的话。
──Et quand tu seras consolé (on se console toujours) tu seras content de m'avoir connu. Tu seras toujours mon ami. Tu auras envie de rire avec moi. Et tu ouvriras parfois ta fenêtre, comme ça, pour le plaisir… Et tes amis seront bien étonnés de te voir rire en regardant le ciel. Alors tu leur diras: "Oui, les étoiles, ça me fait toujours rire!" Et ils te croiront fou. Je t'aurai joué un bien vilain tour…
(然后当你感到宽慰一些的时候(每个人最终都会觉得宽慰的),你会很开心你曾经认识我,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你会开始觉得,你好像又能够跟我一起开怀大笑了。偶尔你会推开窗户,只是为了好玩……而你的朋友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你会一边看着夜空一边大笑,这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告诉他们:「对,是因为那些星星,它们总是让我俊忍不禁。」然后他们就会以为你疯了,这就是我对你开的一个小玩笑……)
「你觉得他现在在星星上吗?你觉得他……你觉得他还会对我笑吗?」迷迷糊糊的,我好像这么问闷油瓶。
闷油瓶没有回答,只是摸了摸我的背,像是在安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轻抚有着令人放松的宽慰,我渐渐平静下来。他把我带着的《Le Petit Prince》,轻轻放在我怀中,让我抱着。
半梦半醒之间,我好像听到三叔在说话。
「你真的关心他。」
「我想为他做的事情很多,但是……」
闷油瓶不知道为什么,停顿了下来,没有把话说完。
我感觉环绕着我的双臂逐渐松开,闷油瓶以细不可闻的声音,似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很高兴遇见你,吴邪。」
那天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最后一个梦。
我梦到我是一隻狐狸,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阳光暖暖的照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又安心又舒服。
而我未曾被驯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