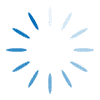元妇宫热气蒸腾,铜盆中的水温暖滑润,独孤后惬意地半仰半坐,任凭加了香料的水抚摩她的胴体。论年龄已是老太婆了,若是乡下女人怕是肉皮早成干树皮了。可作为皇后的她,皮肤依然细腻光泽。毫无遮掩地欣赏自己的玉体,是她最感快慰的事。她陶醉在得意中,就凭这,杨坚也不该再去拥抱别的女人。
侍浴的宫女嘁嘁喳喳,似乎在议论什么。独孤后睁开刚刚眯上的凤眼:“你们在搞什么鬼?”
“禀娘娘,杨素已在门外守候多时,说有要事面奏。”稍远处侍立的刘安赶紧回答。
“要事,要事,来的人都说有要事,我真怀疑人间可还有不重要的事。”独孤后说是说,还是站起身。
两刻钟后,新浴巧妆后的独孤后,焕发着青春气息过来接见恭候的杨素。“叫你久等了,”独孤后心情很好,难得说笑话,“谁让你来的不是时候了。”
“老臣打扰娘娘沐浴,真是罪过。”
“算了,别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套话,有什么事直说吧。”
“老臣是为晋王而来。”
“给他说情?”
“其实是为娘娘。”
“哼,看你能说出几分道理来。”
“娘娘,晋王不能外任。”杨素也就打开了话匣子,“晋王一走,太子得势,万岁易储之念遂消。而娘娘欲以晋王取代太子谁人不知,太子犹为恨之入骨。倘太子因一旦继位,必对娘娘大为不利。保晋王,就是保娘娘自己。”
“倒也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我保他做了平陈元帅,他又如何?脸一黑一毛不拔,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再保他做太子,日后登基,对我还不是过河拆桥。”
“娘娘多虑了!晋王此次平陈未取国宝,老臣一直在场。当时是形势所迫,只能如此,晋王对娘娘是忠贞不二的。太子与娘娘仇隙甚大,只有力保晋王方为上策。”
“看来你也担心太子得势。”独孤后表态了,“你放心出宫吧,我会让万岁改变主意的。”
“娘娘英明。”杨素心情舒展地去了。
独孤后问刘安:“万岁此刻可在武德殿?”
“娘娘是想劝说万岁改变初衷,不把晋王外任?”
“正是,不然明日上朝圣旨一下,木已成舟,就难以挽回了。”
“以奴才之见,还是不说为宜。”
“你这是何意?”独孤后感到奇怪,“晋王待你不薄呀,缘何不为他着想?”
“奴才是既为娘娘,也为晋王,”刘安不无得意,“晋王外任,可收一石二鸟之益。”
独孤后颇感兴趣:“你且仔细讲来。”
“晋王外任,就可验证他对娘娘是否忠心。如上次确因情势所迫,此番镇守扬州,自当将南陈国宝孝敬娘娘。”
独孤后感到有理,不觉点头。
“再者,也可借机考验一下太子,他若认为娘娘无力干预朝政,必然得意忘形,对娘娘愈加不恭。”
“说的是。”
刘安继续说下去:“其实,只要娘娘高兴,什么时候召晋王回京,还不是一句话。”
“好,就照你说的办。”独孤后半嗔半爱地说,“小猴崽子,难怪万岁离不开,鬼点子倒不少。”
“娘娘的夸奖,奴才不敢当。”刘安再次进言,“如今娘娘只静观其变即可,也叫稳坐钓鱼船吧。”
庄严肃穆的金殿,又迎来了大朝之日。诸王子与文武百官垂手恭立,偷窥高踞龙位上的隋文帝,心中的算盘都在急速拨动。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平陈有功的人们,谁不希望加官晋爵获取封赏呢。
圣旨终于从杨坚口中吐出:“晋王平陈有功,加封太尉之职,赐珞车衮冕,玄圭白璧。”
杨广喜不自胜,急忙谢恩。
岂料杨坚又说:“南陈初平,江山未稳,着晋王镇守扬州……”
杨广登时傻了,他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母后已答应杨素,为何突然变卦呢?
刘安见杨广发呆,免不了提醒:“晋王领旨谢恩啊。”
杨广清醒过来,只得叩拜:“儿臣谢恩,父皇万岁!”
太子杨勇却在一旁窃笑,心说看来那微雕玉扇起了作用,母后不再庇护杨广了。他特意向刘安投去感激的一瞥,刘安似乎会意,回报以眼神。
杨素也觉发懵,这是怎么了?独孤后答应好好的,为何言而无信呢?由于走神,以至于文帝对他的封赏都未听到。
“……加封杨素为越国公。”杨坚说罢多时,杨素仍无反应。
秦王杨俊暗中扯动杨素袖子,他才反应过来跪倒谢恩。
接着,杨坚又封高俊为齐国公,李渊升少卿,韩擒虎、贺若弼并进上柱国。对于这一干人的封赏,杨广根本就听不进了。无限的失望,像一张大网把他笼罩。
散朝以后,独孤后照例温情脉脉地与文帝同车并肩回内宫。宝马香车,缓缓行进,发出有节奏的“格登登,格登登”的声响。车外薄寒料峭,文帝越发感到独孤后紧靠过来的躯体软绵绵暖烘烘。他心中至今仍在划问号,原以为独孤后会阻止晋王外任,今日为何竟默不做声呢?
冬日的阳光尤为明亮,文帝突然发现两个熟悉的身影。醒月楼朱栏边那绛紫色和杏黄色的宫妆女,不是陈、蔡二女吗?他刚想吩咐驭车的太监停车,看到独孤后就在身边,又把话噎回去。锦车已驶过醒月楼好远了,文帝仍回头贪恋地注视那绛紫色与杏黄色。
独孤后伸玉掌挡住杨坚视线,半是玩笑半是讥讽地说:“万岁,当心扭伤脖筋。”
文帝有些讪然地转回头,故意打岔:“爱妃,看来你对广儿外任是赞同的。”
“那可不见得。”
杨坚一怔:“那你为何未发议论?”
“为时尚早。”独孤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要看看太子与晋王都是如何动作。”
杨坚感到,独孤后的话就像车外的小北风一样直入肌肤,根本未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那口吻俨然是大隋朝的最高主宰。他不禁打个寒噤,这女人并不温暖,而是像一块坚硬的寒冰。二人一时都默默无言,文帝心生反感,在武德殿径自下车,独孤后是从不服软的人,也不好言劝慰,一个人回仁寿宫去了。
刘安侍候独孤后休息,返身去武德殿听候文帝差遣。近来他是够辛苦了,以往只守在文帝身边一心一意,如今独孤后也要照应,未免经常顾此失彼。帝后和好时他听差还容易些,一逢帝、后闹别扭,也就难为他了。此时他惟恐文帝动怒,一路小跑奔向武德殿。
“刘公公,请留步说句话。”王义迎面挡住去路。
“是你,怎么没随晋王出宫?”
“特来拜访公公。想打听一下娘娘对晋王的态度为何变了?”王义对主人忠心耿耿,恨不能立刻弄明原因。
刘安当然不会透露内情:“此事我也不得而知。”
“刘公公,晋王平素待你不薄呀,人可不能没良心,就凭你我的交情,也该透个话儿。”
刘安登时变脸:“王义,你太过分了!我又不是娘娘腹中虫,怎知娘娘如何想,你去问娘娘好了。”说罢扬长而去。
“你!”王义虽然有气,但亦无可奈何,只得无精打采地去回报杨广。
杨广听了王义回禀,竟一言未发,垂头丧气地回府。而且从路上到府中,始终紧闭双唇。王义几番以话开导,杨广都如未闻,只顾呆呆地想心事。
宇文述闻讯赶来,对于今天这种结果,他确实不曾料到。他面对杨广解释:“杨约不会骗我,这内中定有隐情。”
杨广终于开口了,显然是已经绝望:“如今是说什么也没用了,看太子那得意劲,简直就像做了皇帝一样。”
“千岁无须过于伤感。”宇文述劝解,“事已至此,千岁不当失去信心,可于离京前拜辞娘娘之际,探讨口风,或许娘娘能透露个中缘由。”
杨广叹口气:“便知道缘由又有何用,既放外任太子在朝阻挠,本王休想再有返京之日了。”
“不,只要太子尚未登基,事情就有挽回余地。”宇文述自觉对不起主人,“千岁,卑职决定不随你去扬州赴任,留在京中相机行事。”
“只怕是无济于事。”
“千岁不能灰心,我宇文述便披肝沥胆也要扭转乾坤。”
朔风呜咽,飞雪飘零,战马啸啸长鸣,似乎不耐严寒,急欲飞驰奔腾。杨广仰望一眼阴霾低垂的云空,心头像压了一块铅,甚是沉重。再扫视一遍送行的文武百官,他们杂立在灞桥畔,枯黄的柳枝与杂草败叶不时袭击他们的锦袍,有的瑟缩着脖子,有人抱着双胛,构成了一幅凄怆苍凉的送别图。
杨广今日格外厌烦这无聊的应酬。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里,他率五十万大军南征,旌旗招展,战鼓震天,百官列队,何等威风。然而,今非昔比,虽说是奉旨出镇扬州,又官升太尉高位,但杨广总有一种被流放发配的感觉。不是吗?那高俊、韩擒虎、李渊等人的笑容中,分明都满含着嘲弄。特别是那代表父皇、母后送行的刘安,那皮笑肉不笑的酸样,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奸笑,使杨广心中作呕。此时此刻他不禁想起了昨日下午拜辞母后时的情景。
杨广半是矫饰半是真情地啼泣叩拜:“今日一别母后,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每想及不能晨昏尽孝膝前,五内犹如刀剜。儿臣惟有在扬州任上向北叩拜,祈祷母后寿与天齐。”
“阿摩孝心,为娘尽知。”独孤后见杨广泪珠抛洒,也觉伤感,“你不必过于悲戚,外任未必就是坏事。”
“咳,母后心中明镜高悬,这分明是太子算计儿臣。此一去别无所求,惟愿能保住性命足矣。”
“有我在,谁敢动你一根毫毛。”
“母后,东宫羽翼日丰,惟惧母后一人,儿臣临行之际斗胆忠告,愿母后多加小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只管去吧,我自有道理。”独孤后几番想说些实话,给杨广吃颗定心丸,见刘安一再使眼色,又把话吞咽回去。
杨广一无所获地退出仁寿宫。刘安送到宫门:“千岁走好,恕奴才不远送了。”
杨广心中恨得咬牙,暗说这个奴才,竟这般势利眼。往昔都是送了又送,如今自己尚未完全失势,他就狗眼看人低。但有求于人,只能赔笑脸:“公公逐日在父皇、母后身边,可知本王此去吉凶祸福?”
刘安淡淡一笑:“千岁,奴才可没李靖的本事,不会推算,见谅。”
杨广暗骂,这条狗,以往我算白喂他了。
昨日的情景历历在目,如今杨广看着刘安那大大乎乎的神气样,心中发恨。日后一旦登基,先杀了这个阉竖,以雪今日之耻。他特意向刘安拱手致意:“各位,承蒙专程相送,本王感激不尽,铭记在心,就此分手了,诸位保重,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队列缓缓启动,迤逦向前。送行的百官渐淡渐远,在视野中消逝了,杨广仍未见到所期盼的两个人。按说这二人是理应来送行的,为何竟至今不见呢?难道要背叛自己?杨广失望地合上发酸的双眼,命令队伍加速前进。
道旁土崖下突然跳上两个人,迎面挡住锦车去路。王义机警地拔出短刀:“什么人?”
二人摘去草帽,露出庐山真面目。杨广一见甚喜,挥手令拥过来的武士退下,掀起轿帘探出上身:“你二人到底来了。”
宇文述、杨约双双施礼:“因故来迟,乞请千岁恕罪。”
“何等大事值得宁误送行?为什么躲躲闪闪在这里见我?”
“千岁,我二人正在办一件关乎您能否回京的大事。”宇文述喜形于色,“而且已有眉目。”
“快说说看。”杨广急欲知道。
杨约答话:“天机不可预泄,千岁只管放心赴任,京里一切有我二人。等有了好消息,自然前去报信。”
“怎么,对我还要保密吗?”杨广现出不悦。
宇文述与杨约一样态度:“千岁,若有泄密就可能前功尽弃。况且万一不成,岂不让千岁空欢喜,还是不问为好。”
“说的是。”杨广想起用人不疑的古训,“你二人一片忠心,本王尽知,他年得志,定不吝封侯之赏。”
“士为知己者死,我二人只图报效,不为封赏。”宇文述、杨约异口同声,“长谈多有不便,祝千岁一路顺风,告辞了。”说罢,二人跃下土坎,如飞离去。
杨广猜不透他二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心事重重地挥手令车队继续前进。
耀眼的灯火把销魂窟整个楼院照得通明,悦耳的丝弦声,撩人的浪语淫声,融合在一起飘荡。油头粉面花枝招摇的妓女卖笑门前,连拉带扯地招揽着生意。每一个从门前经过的行人,都是妓女们的猎物,不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掏出来,简直就是罪过。这里是长安城最大的勾栏院,它最大优势在于高中低档俱全,可以满足各种男人的需要。
姬威见宇文述、杨约把他带到这里,登时变了脸色:“二位这是何意?”
“进去坐坐无妨。”宇文述拉住他,“叫几名歌舞妓陪酒,岂不比酒楼有味。”
“你们明知我身体已残,却设圈套诓我来吃花酒,是何居心?”
杨约欲擒故纵:“好,好,姬贤弟,我们决不勉强你。到这来本是我的主意,是想使老弟从心灵痛苦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番好心,你可不该曲解。你实在不进,我可就失陪了。”说罢,径自走入。
姬威尚在犹豫,宇文述连说带劝连拉带拽,硬是把他拖进了销魂窟。
花香、酒香、脂粉香和燃烧的香饼发出的香气,无不由鼻孔钻入五脏。触目皆是女人的红唇、玉白的胸肩臂股、半掩半现的乳峰。充耳皆是调笑狎戏的浪语淫声。特别是在牡丹房中落座以后,杨约、宇文述每人两名美女陪伴,她们旁若无人,裸露放纵,媚态百出。姬威只觉得心肝肺腑拴上了千百只挠钩被人勾扯,他实在难以忍受了,抬手将八仙桌掀翻,可嗓子猛喝一声:“够了!”
四个妓女像同时遭受雷击,全都僵住不动了。宇文述挥手令她们退下。
杨约斜视姬威:“怎么,你下边那物件没有了,还受不住吗?”
“你!”姬威双手揪住杨约脖领,“我整死你!”
宇文述劝道:“姬先生,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被害得男不男女不女,任是谁也受不了这种刺激。”
杨约推开姬威的手:“你是该整死人,但不该是我。”
“是谁给你造成这比死还要难熬的痛苦?”宇文述在引导。
姬威两眼血红:“是太子杨勇!”
“对!是他毁了你一生!”杨约说得明白,“你有种找他算账。”
“我,我!”姬威双眼喷火,“我要杀了他!”
“你冷静一下。”宇文述扶他坐下,“你想过没有,太子戒备森严,你能杀得了吗?”
“他对我不加防备,我杀他个措手不及。”
“杀了太子,你还能活命吗?”
“我,一死足矣。”
“此乃下策。”宇文述开始引他上套,“如果信得过我,愿献一上策,你既能报仇,又丝毫无损,且可建功立业。”
“有这样三全其美的办法?”姬威不信。
“你俯耳过来。”宇文述在姬威耳边低声轻语。
姬威听着禁不住称赞出声:“好,好主意!”
“那你就赶快行动起来,以免夜长梦多。”宇文述从来不失时机。
“弄到毒药,我立即动手。”姬威更是兴致勃勃。
宇文述取出一个纸包:“我已为你准备了。”
姬威紧紧握在手心:“明日我就下手。”
“姬先生英雄也!”杨约举起拇指,“我们重整酒席,开怀畅饮。”
“在下拜辞,我要养精蓄锐准备明日。”
“如此甚好。”宇文述把姬威送出门,“祝你手到成功。”
姬威走后,杨约高兴得笑起来:“宇文先生,你我今夜这出双簧唱得不错。”
宇文述仍有隐忧:“只能说有一半希望,但愿姬威莫露出破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听天由命了。”杨约吞下一杯酒,感到好辣好辣。
元妃一直沉湎病榻,腰肢瘦损,形容憔悴,已有半年之久足未出户了。早晨的阳光红艳艳的,透过碧纱窗照入室内,使元妃这被遗忘冷落的殿堂,平添了几分生气。宫女小桃撩起芙蓉帐,柔声问道:“王妃,是否侍候您起床更衣?”
元妃心中要强,挣扎几下未能坐起:“且过一时再说。”
“也好,待奴婢去花窖采些鲜花来。”小桃出门直奔花园。
正是冬季,园中一片萧杀景象,只有几株松柏挺立着绿色的身躯。花窖在正北,小桃未进园门,看见迎面假山旁有几个人聚在一处,在议论元妃。她赶紧隐身偷眼观望,原来是太子、云妃和唐令则在争论。
云妃手中端个暖食盒,扭捏作态地说:“我不去,我也不比她低气,凭什么去拜望她。”
“哎呀,爱妃。”杨勇有些不耐烦地规劝,“不是说好吗,你是做做样子嘛。”
唐令则却是言辞如铁:“云妃理当前往,你要为殿下着想。”
“是呀,权宜之计嘛。好不容易母后才有了好感,说什么也要应付一下。”
云昭训叹口气:“咳,算我倒楣,看在殿下分上,我就去看看那个小贱人。”说罢,向这里走过来。
小桃飞步回房,告诉元妃:“王妃,云妃来看你。”
“什么!”元妃甚觉突然。
“他们叽叽咕咕,好像很勉强。”小桃尚未说完,云昭训已走进房来。
“元妃姐姐,近来玉体可好?妹妹特来看望。”云昭训来到床前,硬挤出几分笑。
元妃为不失礼,撑着抬起头致意:“妹妹请坐。”
“姐姐患病,妹妹忧心如焚,特意熬了一锅燕窝莲子粥给姐姐补身。”云昭训把食盒放置案头,“小桃,侍候王妃趁热吃下。”
“不急,愚姐尚未梳洗。”元妃有些感动,“妹妹快请坐下叙话。”
云昭训哪有兴趣过多停留:“姐姐尚未更衣,妹妹不多打扰,改日再来看望。”然后,缓缓离去。
元妃吩咐小桃:“快,代我礼送云妃。”
小桃送云妃出了房门仍未停步,又一直向院门送去,岂料她前脚刚走,姬威就闪身钻入房中。姬威是从厨房尾随到这里的,已经跟了好久了。此刻,元妃由于适才劳累,正闭目喘息似睡非睡。姬威悄无声息蹭到案前,伸手去揭食盒盖,小桃送客回转的脚步声响起,姬威情急之下,隐身在床帐侧后。
小桃走到床前,元妃睁开眼睛:“你是刚刚回房吗?”
“对呀。”
“奇怪,适才好像有人进来,难道是我神思恍惚所致?”
小桃立刻警觉:“会是谁呢?”
元妃反劝小桃:“不要当回事,是我的错觉。”
小桃扶元妃躺倒,出门奔花窖去了。姬威不失时机,像猫一样悄声溜出。见元妃处于半睡状态,揭开食盒盖,将纸包中的砒霜抖入,然后用勺子轻搅几下,重又盖好,意欲溜出。
偏偏这时元妃开口问:“小桃,是你回来吗?”说着她睁开眼睛观望,姬威只好又躲入床帐侧后。
元妃不见小桃应声,心中有些纳闷。方才明明感到有人在屋内呀。她挺起身看看,并不见人,心想,难道有鬼魂显灵?还是有窃贼在室?她不敢合眼了,不住左顾右盼。
姬威也就难以脱身了,急得他在床帐后心焦如焚。
小桃手掐一把盛开的水仙花回来,端端正正插入花瓶中,把花瓶捧过来,让元妃嗅嗅花香,元妃不觉引发感慨:“男人都说家花不如野花香,其实家花野花还不是一样香。就说姬威吧,本是殿下亲信,却与云妃私通。”
“王妃,您说的不对。”小桃自有见解,“其实这事全怪云妃,要不是她狐媚勾引,姬先生怎能堕入情网。”
“不是说姬威正对云妃强行非礼时,为殿下撞见吗?”
“那是云妃倒打一耙开脱自己,诬指姬先生强bao,实则是她勾引。”
“若果真如此,姬先生倒是被屈了。”
“其实殿下未必看不透,归根结底是殿下割舍不下云妃那个狐狸精,才拿姬先生开刀出气的。”
“惩戒一下也无可非议,只是殿下也太心狠了。”元妃边说边叹息,“处以宫刑,叫姬先生还如何做人。”
“就是嘛,活不成死不起。”小桃深有同感。
“小桃,此刻姬先生说不定有多么痛苦,等下你代我去看看姬先生,安慰安慰他。再把我的银子拿去一百两,让他增添补品调养身子。钱虽不多,算是我一点心意吧。”元妃说时情真意切。
小桃也动了感情:“王妃真是菩萨心肠,我还攒了十两银子,也送给姬先生吧。”
这主仆的对话,让藏身在床帐后的姬威几乎感动得叫起来,几乎跳出来道谢。这样一个慈悲而又遭到遗弃而处于疾病与心灵双重折磨中的善良女性,自己怎么忍心向她下毒手呢!姬威良心受到极大谴责,他暗暗祈祷上苍,元妃千万不要喝那盆已投了毒的莲子粥呀!
元妃腹中开始蛙鸣般叫起来,小桃知道她早就饿了,便扶元妃半坐起身,然后揭开食盒盖。
姬威那里如同火烧眉毛,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元妃死在自己手中。他迅即脱下衣服蒙住头,飞身跃出,猛一拳击去,食盒扣翻,粥盆跌碎,莲子粥遍地流淌。在元妃、小桃受惊发怔之际,姬威几步蹿出门外,飞跑过花园后不见了。
小桃清醒过来先奔主人:“王妃,您没事吧?”
“小桃,方才是什么人?”元妃受了惊吓,身体更虚弱了。
“没看清,您两次说有偷儿,果然有贼。只是不知是府内坏人还是府外歹徒?”
“他将粥盆打翻在地是何用意呢?”元妃感到奇怪。
小桃在这方面没有多想,而是问:“王妃,是否去报告殿下,让他下令搜捕歹人?”
元妃沉吟片刻:“算了,歹人是为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也未伤害我们,何苦与其作对,由他去吧。”
“王妃,您总是这样心眼好。”小桃无限感慨,“奴婢担心,您将来吃亏就吃在这上面。俗话说‘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寿齐天’哪!”
“俗话还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心总有好报的。”
“咳,真拿你没办法。”小桃蹲下身去收拾屋地上一塌糊涂的残局。
残雪消融,野草返青,杨柳枝在东风的抚摩与暖日的吻照下,已绽出如苞的绿芽。而宇文述与杨约的心情,并未像春天那样蓬勃轻盈,而是如严冬一样冰封雪冻般沉重。精心策划的借刀杀人计,满以为势在必成。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姬威从分手后就再未露面。宇文述几乎天天在太子府门外等候,可姬威就是不越大门一步。后来宇文述从侧面获悉,姬威与元妃过从甚密,二人大有彼此相怜之意。常在一处谈诗论画,似乎彼此遇到了知音。二人的心情都比过去开朗了,久病的元妃精神也转好。这使宇文述越发忧心忡忡,看来要姬威投毒害死元妃是很难做到了。但是,元妃不死,下一步计划就全要落空,又难以向晋王交待。绞尽脑汁,他与杨约才又想出一条妙计,仍要借姬威之手除掉元妃,然后再牵着姬威鼻子走。妙计议定,宇文述耐下性子,在太子府大门外守候。守株待兔固然是个笨法,但舍此无路可走,他深信,总有一天姬威要走出大门。
机会终于来了!这日上午,姬威摇摇晃晃出了太子府大门。宇文述喜不自胜,但他未轻举妄动,悄悄在后跟随,直到大街之上,四望确信没有太子府人,才靠上前去,当面一揖:“姬兄别来无恙。”
姬威一怔,扭头要躲走。
宇文述一把拉住他:“这样对待老朋友未免太无情了。”
姬威硬着头皮回礼:“原来是宇文兄,小弟还有急事,失陪了。”
宇文述拉住不放:“数月不见,渴思甚矣。你我何不到酒馆小坐,畅饮一番,以叙别情。”
姬威料到难以脱身,只好随宇文述登上醉仙楼。在雅间落座后他还急于脱身:“宇文兄,我不能久坐。”
宇文述满口答应:“好说,三五杯就放你走。”
姬威心怀鬼胎,因为答应过投毒致元妃于死地,如今竟言而无信,他感到难为情,在盘算如何解释。宇文述并不急于触动姬威心病,只是一味劝酒让菜。待酒过三巡,才引话入正题:“姬兄,听说你与元妃已成莫逆之交?”
“哪里。”姬威否认,“不过是彼此都为太子殿下所弃,同病相怜,接触略多而已。”
“所以姬兄就不忍下手了?”
“宇文兄,我的仇人本是太子,而元妃又深为同情我的遭遇。你说说,我怎能平白害死一个无辜的女人?她已经够可怜了。”
“姬兄之言,合乎情理。我与杨兄都不责怪你,算了,那件事就此做罢,那包药你倒掉算了。”
姬威没想到宇文述这样通情达理:“宇文兄,我自食其言,甚觉不安,有负二位。难得谅解,请受我一拜。”站起,深深一躬。
宇文述拉他坐下:“快莫如此,我们还是好兄弟,那件事莫再提起。来,干了这杯。”
姬威心头乌云被驱散,兴致高涨,遂与宇文述畅饮起来。渐渐已有七分醉意,宇文述感到时机成熟,要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未完待续)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